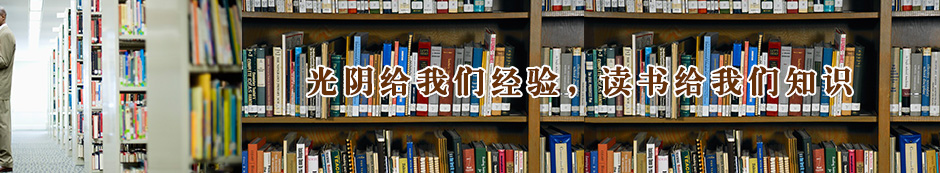[摘要]“我去中国的一些地方,看到成百上千年留下来的传统建筑被冠以‘危楼’之名很快拆掉,代之以毫无特色的通用楼群。作为旁观者,我也感到伤心。”
腾讯文化 张璐诗 发自广东深圳
伊万·巴恩抓拍展览现场的列队保安 拍摄:张璐诗
“可别叫我建筑摄影师。”衬衫外套着皮夹克的荷兰摄影师伊万·巴恩(Iwan Baan),领腾讯文化作者去看他在2015深港建筑城市双城双年展上的摄影展位。下楼看见保安们在主展场前列队训练,伊万·巴恩就从兜里掏出智能手机,连拍了好几张。当时我们刚好在讨论即时数码摄影,伊万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:“它给了人们莫大的自由。人人都能够记录下此时此地发生的事,而且大家都能拍出好照片来。”
伊万·巴恩是当今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摄影师之一。他的独到之处是将建筑摄影演绎成纪实摄影,呈现世界各地人居环境中人与建筑的关系。这一尝试始于10年前。当时他认识了大都会建筑事务所(OMA)的首席建筑师库哈斯,后者对他的交互式全景摄影(Interactive Panoramic Photography)很感兴趣。很快,伊万·巴恩跟随库哈斯来到北京,开始跟拍后者设计的CCTV新大楼。这是他的第一个大型创作项目。
伊万·巴恩拍摄的央视大楼
几乎与此同时,受赫尔佐格-德梅隆建筑事务所委约,伊万·巴恩开始跟拍北京奥运会场馆“鸟巢”。自此,他的图片常见于《纽约时报》等媒体,其作品也被誉为“重新定义了建筑摄影”。他逐渐获得了建筑摄影界最高奖——朱利安·舒尔曼奖,并与扎哈·哈迪德、伊东丰雄、王澍、斯蒂文·霍尔等各国著名建筑师长期合作。
伊万·巴恩现在一年会到访中国4-8次,而这次是他首度正式参加深港建筑城市双城双年展。在挨着蛇口港的展厅——一个改造后的旧面粉厂大楼内,他在世界各国旅行时用手机拍摄并发在图片社交媒体Instagram上的照片,被打印在与墙等高的一匹匹布上,像窗帘一样挂起来,每幅照片旁还印着点赞人数和评论。伊万·巴恩说,这次自己原本计划到珠三角各处拍摄,但因为时间与资金的紧张而作罢。
以下为腾讯文化与伊万·巴恩的对话。
计划拍摄中国城中村
伊万·巴恩 拍摄:Jonas Eriksson
腾讯文化:在你看来,一个摄影师可以发挥什么样的潜力?
伊万·巴恩:摄影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财富。以建筑师看待未来的视角作为叙事的基础,摄影师可以展示一个人们平时可能看不见的世界。我有一个拍摄城中村的计划,准备以后到中国各地去拍摄。
腾讯文化:这个计划如何开展?
伊万·巴恩:我觉得这是个迫切需要去跟进的项目,但暂时还没有很周详的计划。我猜测,这需要通过中国相关部门去联系拍摄吧。
腾讯文化:你是在中国拍摄才感觉到这种迫切吗?
伊万·巴恩:世界各地都一样。我受委约去拍摄当代建筑项目时,都会问: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、在这个城市,需要有这样一个建筑项目。
腾讯文化:可是你抗拒别人叫你“建筑摄影师”。
伊万·巴恩:我不喜欢。(腼腆笑)如果光拍建筑,借助日落的光线就能拍出好片子来,但在我的镜头里,建筑工程只是照片的组成部分而已——虽然因为语言障碍,我跟当地人聊天不太多,但通过观察,我能了解到眼前这些人都正在做些什么,他们为什么在这儿而不是在那儿。通过捕捉在建筑周围的人的动静,我常常就能侧面讲述这个建筑的前世今生。
腾讯文化:你在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都拍摄过。在这两种地方拍摄,有什么区别?
伊万·巴恩:确实有些区别,但我在照片中尽量不去呈现这些区别,而是采用另一种调子: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、是什么样的人,生活对他们来说都很平常。
比方说,住在纽约一间要价900万美元的公寓里,对有些人来说是平常的。在工地上为他人建造不属于自己的大楼,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也是平常的。大千世界,在不同环境下自有不一样的“平常”。
用7年时间跟拍CCTV
伊万·巴恩拍摄的央视大楼
腾讯文化:你曾多年跟拍CCTV新楼和“鸟巢”。图片刊发后,你有没有得到过来自中国官方的反馈?
伊万·巴恩:拍摄CCTV时,大部分场地是不让外人进的,我主要是跟建筑师对接。库哈斯随便我拍照,怎么拍完全出于我自己的诠释。拍了这么多年,我从没有听说过任何来自中国官方的反馈呢。
受委约做创作时,我只与个体合作。无论涉及的是政府开发商、建筑师还是个人,他们一向都给我充分的自由。我就是负责去记录我看到的。我从来没有一张什么可以拍、什么不可以拍、怎么去拍的清单。如果是这种项目,我是不会去参与的。
腾讯文化:跟拍CCTV新楼的项目是怎么开始的?你如何去选择拍摄角度?
伊万·巴恩:2005年,我开始跟拍库哈斯的CCTV新楼时,那里还什么都没起来。最初引起我兴趣的,是中国这种规划未来的高瞻远瞩与行动力——在中国城市最需要对建筑的想像力的时刻,中国政府很及时地委约了多位国际建筑设计师来工作。
对我来说,记录下这些时间段里发生的故事,非常重要。我不光是拍摄建筑本身,也拍摄整幢楼是怎么建起来的。CCTV新楼的工地上当时有1万个建筑工人,这在西方是很难想像的。我知道这些工人都来自小村庄,为打工到城市里待上几年。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,与自己熟悉的一切完全隔离开,这是很难去想像的生活。
我们曾经计划跟着其中的一些工人回农村去,拍摄他们的家乡,记录这些移民者的生活。可惜在中国做每件事都需要太多的前提条件。而且由于语言障碍,我一直都没能跟工人好好交谈。
在中国,什么都很多,建筑工人的数量是这样,正在进行建设的城市也是这样。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很难看到如此大规模和高速的建设。这令我想通过拍照去反映未来几十年里,世界其他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。
腾讯文化:你最后一次在CCTV新楼拍片是什么时候?北配楼大火后,那里一度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。
伊万·巴恩:对于CCTV新楼,我一直跟拍到2011年所有的设备和家具都搬进去为止。在大火以后,我只去过一次——工作人员开始在里面工作后,建筑师没有了从前控制大局的权力,我也就很难再进去了。但我还是很想在北配楼完全建好以后再去拍片,有可能在明年初吧。
伊万·巴恩拍摄的“鸟巢”
对中国的“拆”感到伤心
伊万·巴恩拍摄的宁波历史博物馆。它的设计者是中国建筑师王澍
腾讯文化:你跟王澍是怎么开始合作的?
伊万·巴恩:大概8年前,我们在纽约的一场中国建筑师群展上认识。那时他不怎么会说英语,我们完全靠手势来交流。我在他的作品中,立即就能认出那种熟悉的迫切感。他会有意识地去结合传统中国建筑和当代的建筑理念,他的每一个建筑方案也都是针对特定城市、环境和人群的。
腾讯文化:你多年跟拍、见证中国的城市建设。西方观众看过这些照片后,有怎样的反应?
伊万·巴恩:这些照片对很多人的冲击力挺大。大家看到,在如今的中国,能实现在别的地方所无法实现的事情。我想,这是因为在中国,做什么决定都是由上而下的,决策者说了在这个地方起这么一幢楼,就肯定会实现。或者有人有足够的金钱和权力,说做就做了。权力与建筑的高效性有如此密切的关系,在我们看来是很有意思的事。
像CCTV、“鸟巢”这样的大型项目,在西方是绝对不可能建起来的。因为项目策划案出来后,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个人和团体以不同利益的名义去干预,这样一来,项目就慢慢被推翻了。
腾讯文化: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早就有“当代建筑实验场”的称号。
伊万·巴恩:你看,99%的中国城市建筑都是毫无特点的通用楼群,建筑设计上一点都没有想像力,也完全找不到设计者、规划者的名字。这是最令人黯然的。在当代建筑设计师的群体中,确实有风格极端的建筑师,满脑子疯狂的点子,可退一万步来说,至少他们都在发挥有创造性的想像力,对于满眼都是通用建筑的城郊、乡村,这尤其可贵。
腾讯文化:当代建筑的外观美和实用性,也是一个经常引发讨论的话题。
伊万·巴恩:当然,新事物总会有慢慢与环境磨合的过程。可尽管当代建筑有时会遇到实用性不够的问题,从当今世界各地的城市规划格局来看,有当代建筑师在不断实验,总归是有意思的事。
我在这次深港双城双年展的讲座上给大家展示过非洲的好几个地方,当地的人居环境一度跟半个世纪前没什么区别。那里后来成了当代建筑设计师的“游乐场”,后者尝试不同的设计方案,帮助当地人一起重新去想像:在老房子的基础上,一个新的居住环境可以是什么样的。由这些设计师们帮助翻新的建筑,最终肯定会让当地人的生活更方便,也绝对比毫无想像力的通用建筑好得多。
伊万·巴恩拍摄的北京银河SOHO。它的设计者为扎哈·哈迪德
腾讯文化:你拍过河南的天井窑院、福建土楼和徽派建筑。传统建筑在中国在逐渐消失,你要记录的话,怎么去寻找?
伊万·巴恩:对我来说,这确实是个难题。我只能通过现有的一些关系和认识的一些艺术家,再间接去请当地人带我慢慢找。如今整个中国都在建一模一样的楼,可是如果往回看,中国建筑具有如此的多样性,不同区域有自己的建筑风格,这些风格的形成与气候、材料等当地性互相依存。
可是这些全都被抹掉了。我去中国的一些地方,看到成百上千年留下来的传统建筑被冠以“危楼”之名很快拆掉,代之以毫无特色的通用楼群。作为旁观者,我也感到伤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