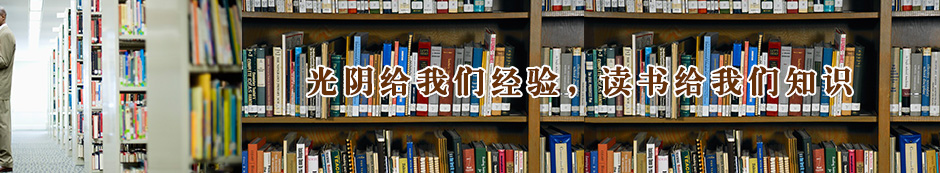[摘要]传统社会从来就不认为女性应该拥有选择命运的权利,现代社会也时不时颂扬女知青被迫嫁给农民这类畸形婚姻,所以,有郜艳敏这样的宣传报道,并非怪事,因为“我大中国自有国情在此”。
导语:
近日,被拐妇女、“临时代课教师”郜艳敏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焦点,舆论风暴之下,郜艳敏表示希望生活平静,接受《新京报》采访时表示应该抓人贩,不该指责她的家人,而下岸村村民更指责郜艳敏被媒体报道导致村里光棍娶不到媳妇,为什么郜艳敏和村民们有如此观点?这源于传统习俗将女人视为玩物,强调女人守妇道,更源于上山下乡时对女知青被迫嫁给农民的正面宣传。
郜艳敏(图源网络)
男人沦为弱势群体备受践踏女人更甚
不论怎么书写历史,都无法回避中国人人性中的阴暗一面,坦然面对人性的阴暗面,才能治病救人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并非都是温情与敬意,史料中隐藏着无数残忍的事实,而这些事实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
比如,将健康的人制作成“人狗”“人熊”,以博取看客的关注,赚取钱财。《清稗类钞》记载:“乾隆辛巳(1761),苏州虎丘市上有丐,挈狗熊以俱。狗熊大如川马,箭毛森立,能作字吟诗,而不能言。往观者施一钱,许观之。以素纸求书,则大书唐诗一首,酬以百钱。”
据这个人所言,他是被乞丐骗去弄哑了嗓子,刺破皮肤,趁着血热时将刚剥下的狗熊皮套在他身上,使他不能脱掉狗熊皮,成为“人熊”,以此骗取钱财。
除了这种方式外,乞丐还会将婴儿放在大缸里养,造成其四肢萎缩,脑袋变大,以此吸引好奇的看客,赚取钱财。而这种方式,即便今天也一样存在,不少行乞之人将婴幼儿折磨成残疾,骗取大众同情心。
在传统社会中,乞丐本是弱势群体,但他们会践踏更弱势的人,以此谋财。民间如此,官方也未必好太多,以宋代为例,宋代推行义冢制度,朝廷规定守园僧人“以所葬多为最,得度牒及紫衣”,守园僧人“遂有折骸以应数者”,以便冒领“恩例”。某些地方官员居然“责保正长以无病及已葬人充”。无病就埋,也就是活埋,而这些人顶多就被杖责一百,人命之低贱可见一斑。
人命不值钱,一个男性如果沦为弱势群体,也会受到极端严重的践踏,相比于男性,女性则更容易沦为弱势群体,在男性都无法保护自身的情况下,女性更无法保护自己,战乱时期,女性往往沦为军妓,乃至军粮,成为所谓的“不羡羊”。
正常社会妇女也被视为男人附属要守贞
当然,古代社会也有太平时期,这个时候,妇女往往会被视为男性附属品,隋唐以前,妇女尚有一定地位,离婚改嫁并非难事,汉武帝的母亲也是改嫁之人,但是隋唐以后,男人们便开始强调女人遵守妇道。
唐太宗亲自撰写《女训》十三卷,强调妇女要遵从三从四德,唐太宗死后,他的小妾都出家感业寺为尼,连武则天也不例外,尽管后来武则天勾搭了李治,当上皇帝,但至少从唐太宗的角度而言,妇女应当遵守妇道。
柳宗元在《河间传》中说:“闻妇之道,以贞、顺、静、专为礼。若夫矜车服耀首饰,族出欢闹以饮食观游,非妇人宜也。”也就是说,柳宗元认为妇女应该安静地呆在家里,外出旅游不是该干的事。李翱《杨烈妇传》进一步说明:“于卑幼有慈爱,而能不失其贞者,则贤矣。”也就是说保持贞操,女人才能称为贤。
孟郊在《烈女操》中更直言不讳地歌颂说:“贞妇贵殉?夫,舍生亦如此。波澜誓不起,妾心古井水。”在他看来,值得称道的妇女不但要守贞,最好夫君死了自己去殉葬。
由于政府和文人的提倡,唐代已经出现各种贞洁烈女,《太平广记》记载,唐朝卫敬瑜的妻子年纪十六岁时丈夫就死了,她割掉耳朵立誓,决不改嫁。女人为了守贞,不惜以自残为代价,可见在唐代,女人已经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属品,守贞成了一种社会追求。
宋代以后,要求妇女守贞之风更甚,欧阳修创造了千古名句“人言嫁鸡逐鸡飞,安知嫁鸠被鸠逐”,也就是女人嫁了丈夫,不管他是鸡是狗,也要跟随始终,曹雪芹将这句话演绎成“嫁稀随稀,嫁叟随叟”,最终变为“嫁鸡随鸡嫁狗随狗”,这句话实为中国女人的命运写照,她们没有选择权,只是男人的附庸。
作为男人的附属品,《水浒传》中的扈三娘堪称典型代表,她全家都被梁山杀了,还要听从仇人宋江的安排,嫁给又丑又矮的王英,最后还跟这个人死在一处,作为男人的玩物,这似乎就是她注定的下场,至于她在想什么,谁会去关心?
近代妇女解放不深入 妇女能顶半边天指劳动
近代以来,中国掀起数次妇女解放运动,力图改变妇女作为男人附属品的地位,也涌现出不少杰出女性,如革命者秋瑾,作家张爱玲,学者林徽因等,但近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并不深入,更多地集中在精英阶层和大城市中,对广大农村和中下层妇女而言,解放并未发生。
举例而言,鲁迅的母亲为鲁迅安排了一门亲事,鲁迅在得知母亲的决定后,回家作坚决斗争,誓死反抗,最后娶了学生许广平,朱安则成为鲁迅反抗的代价,一生与寡妇无异,命运实为悲惨。
同样的案例,也发生在林彪身上。林彪8岁那年,父母为他找了个童养媳汪氏,1927年,北伐途中的林彪回乡成婚,但这门婚事并非他所想,于是成亲当晚就返回部队,并给父母写信表达自己的意思,劝汪氏改嫁他人,汪氏接信后痛哭几天,当众发誓此生永不改嫁,守了一辈子活寡。实际上,从朱安和汪氏身上,看不到任何近代妇女解放的痕迹,她们依然是男人的附属品。
不过,相比于张灵甫第一任妻子吴海兰,汪氏和朱安是幸运的,毕竟她们没有生命之忧。张灵甫早年娶妻吴海兰,因为行军打仗,夫妻分隔两地生活,感情生隙,张灵甫听到风言风语便认为妻子不忠(也有说法认为张灵甫觉得妻子是“共党”,但不论如何,私自杀人都是犯罪),回家将其枪杀,成为民国轰动一时的大案,张灵甫坐了几年牢后重返军队,成了蒋介石口中的“模范军人”。
可见在张灵甫的眼中,女人对自己不忠便是死罪,杀了人,无非是坐几年牢罢了。
从以上事例不难看出,民国的妇女解放运动,并不深入,女人的地位没有实质性提高,作为男人从属品的地位并未改变。
新中国成立后,毛泽东提出了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的口号,不过这句话更多是从劳动角度而非权利角度而言,引用毛泽东这句名言不能不考量其提出的时代背景:20世纪50年代农业生产大热潮时期,贵州贵阳市息烽县养龙司乡堡子村最初并非男女同工同酬,当时的妇女主任易华仙提出:“毛主席都说男女平等了,女社员也应该出工,并且工分要和男社员一样多。”于是易华仙带领妇女和男社员一起下田犁土、插秧。1955年,贵州民主妇女联合会刊物发表《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酬》的文章,表彰实行男女同酬的堡子村。毛泽东看到文章后亲批:“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”。之后,毛泽东提出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的口号,迅速响彻大江南北。
因此,这个口号对应的是号召妇女参加劳动,尽管涉及权利层面,但也未能解决妇女是男人附属品的问题。
上山下乡中女性附属品的定位再次凸显
等到上山下乡运动开展时,中国女性的附属定位再次展现无遗,与男学生一样,女学生也要参与上山下乡运动,无力决定命运,更悲惨的是,为了配合政策宣传,许多女知青被迫与贫下中农结合。
河北师范大学毕业生白启娴,1968年前往沧州相国庄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在这个大队,因为一句玩笑话,嫁给了当地农民毕振远,白启娴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,但这并不妨碍媒体对她的称赞。1974年2月7日,《人民日报》刊发题为《敢于同旧传统彻底决裂》的文章,颂扬白启娴敢于同传统观念决裂,号召更多人向她学习。
尽管白启娴努力配合宣传部门的宣传,将自己原本凑合的婚姻很真诚地升华到了“路线斗争”的高度:“爱上农村,爱上农民,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了我,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了我,是贫下中农教育了我。”但这并未能使她过上幸福生活,也没能阻挡她积劳成疾。
1981年12月,白启娴打算离婚,但因孩子的缘故未能实现,1982年11月白启娴在痛苦中去世。与白启娴相同的案例,并非少数。知青史研究专家刘小萌在谈及女知青被迫嫁给农民时,反对肯定这种畸形婚姻,然而他的意见并未被采纳,2014年3月1日,《重庆晚报》刊发文章《重庆女知青张芬:嫁给深山农民的39?年》,文中称张芬39年前嫁到深山农村,但从未后悔过,该文结尾这样描述到:“简陋的屋里,顿时充满快活的空气。”
这种报道其实与郜艳敏的报道有不谋而合之处,都将女人视为附属品,都肯定一种本不该发生的畸形婚姻,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女人作为人的权利。
其实,中国传统中,个人的权利就是缺失的,男性尚且谈不上拥有权利,女性则更没有,碰上战乱,女性会被随时杀掉乃至吃掉,等到男人和政府开始提倡女性守妇道后,女性就彻底沦为男人的附属品,此后千余年,女性的这种角色定位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。
传统文化与习俗要求女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,要求女性遵从命运不要反抗,因此才会有媒体去歌颂嫁给农民的女知青,歌颂被拐妇女成为乡村教师,而传统的影响,使女性甘愿认命,接受这样的安排,而没有意识到权利被侵害,所以郜艳敏说出不希望公公被惩罚,是非常自然的表现。
实际上,直到今天,多数人潜意识中都认为女性是附属品,所谓的男女平等,在大众层面上远未实现,很多时候,女性被视为财产,结婚嫁人,都需要彩礼房子,从未将女性视为有权利的自然人。
传统社会从来就不认为女性应该拥有选择命运的权利,现代社会也时不时颂扬女知青被迫嫁给农民这类畸形婚姻,所以,有郜艳敏这样的宣传报道,并非怪事,因为“我大中国自有国情在此”。
结语:
鲁迅在《狂人日记》中写道:“我翻开历史一查,这历史没有年代,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,仔细看了半夜,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,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!”其实今天依然。